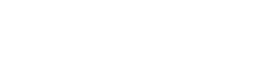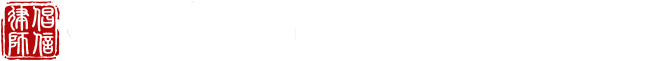2020年至2023年,安某和高某戀愛期間,高某多次以償還貸款、做手術、購買物品等借口頻繁的向安某借款,截止2023年2月23日借款共計270706元時,安某才發現高某已婚,得知被欺騙后,要求其返還借款本金未果,無奈之下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楚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。
訴訟中,高某辯稱,安某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依據與法律依據,兩人戀愛期間的轉賬往來屬于兩人情感的自愿贈與和共同花銷,而非借款,雖然兩人現在已經分開,但分手并不是撤回贈與的必要條件,安某無權變相撤回贈與要求其返還。
經法院審理查明,根據雙方微信聊天記錄,安某多在高某需用錢時候主動轉賬,雙方并無借貸合意,不構成民間借貸法律關系。贈與合同是贈與人無償將財產給予受贈人、受贈人表示接受該合同,同時民事法律行為可附條件,所附條件需具有未來性、或然性、非法定性以及合法性。安某稱戀愛期間轉賬是以結婚為目的,法院認為三年內轉賬金額達270706元,并非單純贈與,實為附結婚條件之贈與,屬附條件贈與合同糾紛。現在雙方已經分手,結婚目的未能實現,受贈人高某應根據實際情況予以適當返還。
高某于2022年10月離婚,安某于2021年11月知悉高某已婚。安某在明知高某有配偶的情況下仍與其保持戀愛關系,該行為違背公序良俗及夫妻忠實義務,同時也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。因此,法院酌定,高某應返還安某在其離婚前所獲轉賬共計236006元。高某離婚后安某的轉賬屬自愿贈與,是對其自身權利的處分,法院不予支持返還。
一、事前預防:幫當事人規避 “轉賬即贈與” 風險
安某在戀愛期間多次向高某轉賬,若提前咨詢律師,可避免后續維權被動,律師此時可充當 “風險預警者”:
明確轉賬性質:向安某解讀 “普通贈與” 與 “附條件贈與” 的法律區別,提醒其若以結婚為目的轉賬,需通過聊天記錄、書面約定等方式留存 “以結婚為前提” 的證據(如明確提及 “這筆錢是為了我們以后結婚用”),避免后續高某以 “自愿贈與” 抗辯;
審查關系合法性:若安某咨詢時透露高某可能已婚,律師可協助核實高某婚姻狀況(如通過民政部門查詢),明確告知其與已婚人士保持戀愛關系違背公序良俗,不僅可能導致轉賬難以追回,還可能引發道德與法律風險,及時止損。
二、訴訟階段:厘清法律關系,為當事人爭取合理返還
安某發現被騙后起訴,高某以 “自愿贈與” 抗辯,此時律師是 “法律論證者” 與 “證據組織者”:
證據梳理與定性:協助安某整理三年間的 27 萬轉賬記錄,結合微信聊天記錄(如高某借款理由、雙方對未來的規劃),論證轉賬并非 “單純贈與”,而是以結婚為條件的附條件贈與 —— 重點突出轉賬金額大、持續時間長,符合 “為促成婚姻而付出” 的特征,反駁高某的 “共同花銷”“自愿贈與” 主張;
法律適用與風險提示:向安某明確 “明知對方已婚仍保持關系違背公序良俗” 的法律后果,預判法院可能對 “離婚前轉賬” 與 “離婚后轉賬” 區別處理,避免安某對返還金額產生過高預期;同時依據《民法典》關于附條件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,主張 “結婚目的未實現,高某應返還附條件贈與款項”,為庭審辯論奠定基礎。
三、判決后:解讀結果與后續應對
法院最終判決高某返還離婚前 23.6 萬轉賬,律師需做好 “結果解讀與權益保障者”:
判決結果解讀:向安某解釋法院酌定返還的邏輯 —— 既認可 “附條件贈與” 的性質,又考量其 “明知對方已婚仍保持關系” 的過錯,故僅支持離婚前轉賬返還,幫助安某理解判決合理性,避免因誤解引發后續糾紛;
協助執行與風險防范:若高某未按判決履行返還義務,律師可協助安某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,確保 23.6 萬款項足額追回;同時提醒安某后續戀愛中,涉及大額轉賬需提前明確性質、留存證據,避免再次陷入類似法律糾紛。
總結:律師不是 “幫人全額追回”,而是 “在法律框架內爭取最優權益”
在安某這類戀愛附條件贈與糾紛中,律師的核心作用是 “厘清法律邊界”—— 既不夸大維權結果,也不忽視當事人過錯,而是通過梳理證據、適用法律,幫助當事人在 “附條件贈與成立” 與 “自身過錯影響” 之間找到平衡點,最終爭取到合理的返還金額,同時引導當事人認識到法律對 “公序良俗” 的維護,避免未來再犯類似錯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