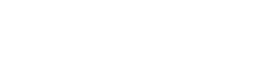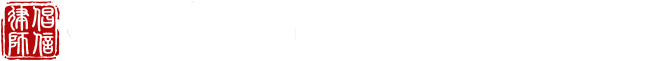王先生與張女士于2001年登記結(jié)婚,并于2002年生育一女王粒,2007年雙方以王粒名義購買案涉房屋,后王先生與張女士離婚,最終王粒由王先生撫養(yǎng)。離婚訴訟后,王先生于2016年以王粒代理人身份與自己簽訂贈(zèng)與合同,將案涉房屋無償贈(zèng)與自己,后自行辦理過戶登記并出售案涉房屋。
王粒主張父親為其監(jiān)護(hù)人,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,非法處分其名下房產(chǎn),侵犯了未成年人合法權(quán)益,故訴至法院,要求確認(rèn)贈(zèng)與合同無效以及賠償無法返還房屋所造成的損失1160萬元。北京市海淀區(qū)人民法院經(jīng)審理,認(rèn)定王先生自行簽署的贈(zèng)與合同侵害了王粒的合法權(quán)益,有悖公序良俗,支持了王粒的請求。
原告王粒訴稱,2007年,我獲得案涉房屋所有權(quán),2016年父母離婚判決書中載明案涉房屋系我個(gè)人財(cái)產(chǎn),而非父母的共同財(cái)產(chǎn)。2023年我在不動(dòng)產(chǎn)登記中心得知,父親王先生已于2016年8月代表我與其簽訂案涉房屋的贈(zèng)與合同,并將該房屋過戶至其名下,該行為侵害了我的合法權(quán)益,故訴至法院請求確認(rèn)贈(zèng)與合同無效并賠償損失1160萬元。
被告王先生辯稱,案涉房屋過戶系用于貸款獲取資金,該資金已用于王粒留學(xué),系考慮王粒利益所為;另外,離婚后財(cái)產(chǎn)糾紛案件判決我需支付張女士款項(xiàng),所以我出售案涉房屋用于獲取資金。
第三人張女士述稱,案涉房屋系登記于王粒名下,僅在雙方離婚后數(shù)日內(nèi)王先生便辦理贈(zèng)與過戶手續(xù),后將該房屋出售給案外人,該行為屬于侵害未成年人財(cái)產(chǎn)的行為,王先生所述出售房屋系為王粒利益,與事實(shí)不符。
法院經(jīng)審理后認(rèn)為,案涉房屋系王粒個(gè)人財(cái)產(chǎn),王先生與張女士離婚糾紛、離婚后財(cái)產(chǎn)糾紛中,均未作為夫妻共同財(cái)產(chǎn)予以分割;王先生通過自行簽署贈(zèng)與合同的方式,將被監(jiān)護(hù)人王粒個(gè)人名下案涉房屋轉(zhuǎn)移登記至其個(gè)人名下,其作為王粒的法定監(jiān)護(hù)人,在作出與被監(jiān)護(hù)人利益有關(guān)的決定時(shí),未征求王粒本人意見,未尊重被監(jiān)護(hù)人的真實(shí)意愿,侵害了王粒的合法財(cái)產(chǎn)權(quán)益,且有悖公序良俗。
從離婚糾紛、離婚后財(cái)產(chǎn)糾紛案件所查明的王先生名下財(cái)產(chǎn)情況來看,王先生所述舉債資助王粒國外留學(xué)的抗辯意見,缺乏事實(shí)依據(jù),由此確認(rèn)贈(zèng)與合同無效。民事法律行為無效、被撤銷或者確定不發(fā)生效力后,行為人因該行為取得的財(cái)產(chǎn),應(yīng)當(dāng)予以返還;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,應(yīng)當(dāng)折價(jià)補(bǔ)償,故王先生應(yīng)按照房屋實(shí)際成交價(jià)款補(bǔ)償王粒相應(yīng)損失。法院最終作出上述判決。
宣判后,王先生提起上訴,二審法院維持原判,該判決現(xiàn)已生效。
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監(jiān)護(hù)人濫用職權(quán)侵害未成年人財(cái)產(chǎn)權(quán)益案件,核心圍繞 “監(jiān)護(hù)人自我交易的法律效力”“被監(jiān)護(hù)人財(cái)產(chǎn)保護(hù)”“公序良俗原則適用” 三大法律問題展開。以下結(jié)合判決邏輯與法律依據(jù),對案件關(guān)鍵要點(diǎn)進(jìn)行深度拆解:
法院首先明確房屋所有權(quán)歸屬,這是后續(xù)法律分析的基礎(chǔ) ——
物權(quán)登記的公示效力:根據(jù)《民法典》第二百零九條,不動(dòng)產(chǎn)物權(quán)的設(shè)立、變更、轉(zhuǎn)讓和消滅,經(jīng)依法登記發(fā)生效力。本案中,房屋于 2007 年以王粒名義購買并完成登記,王粒自始取得房屋所有權(quán),且在父母離婚訴訟中,法院明確該房屋不屬于夫妻共同財(cái)產(chǎn)。
贈(zèng)與行為的不可撤銷性:父母將房屋登記在未成年子女名下,本質(zhì)上是贈(zèng)與行為。根據(jù)《民法典》第六百五十八條,贈(zèng)與財(cái)產(chǎn)權(quán)利轉(zhuǎn)移后,贈(zèng)與人通常不得撤銷贈(zèng)與。本案中,房屋已完成過戶登記,贈(zèng)與行為生效且不可撤銷,王先生無權(quán)擅自收回。
監(jiān)護(hù)人的法定職責(zé)邊界:王先生作為監(jiān)護(hù)人,對王粒的財(cái)產(chǎn)僅享有管理權(quán),而非所有權(quán)。其行為必須嚴(yán)格限定在 “維護(hù)被監(jiān)護(hù)人利益” 范圍內(nèi),不得擅自處分財(cái)產(chǎn)。
王先生以監(jiān)護(hù)人身份與自己簽訂贈(zèng)與合同,將房屋轉(zhuǎn)移至自己名下,這一行為在法律上構(gòu)成自我交易,其效力需從以下維度分析:
違反監(jiān)護(hù)人忠實(shí)義務(wù):
根據(jù)《民法典》第三十五條,監(jiān)護(hù)人履行職責(zé)時(shí)應(yīng)遵循 “最有利于被監(jiān)護(hù)人” 原則,除為維護(hù)被監(jiān)護(hù)人利益外,不得處分其財(cái)產(chǎn)。王先生的行為明顯屬于無權(quán)處分,且未舉證證明處分行為與王粒利益相關(guān)。
從行為動(dòng)機(jī)看,王先生在離婚后數(shù)日內(nèi)迅速辦理過戶并出售房屋,結(jié)合其名下其他財(cái)產(chǎn)狀況,法院有合理理由懷疑其行為系逃避離婚財(cái)產(chǎn)分割或個(gè)人債務(wù),而非為子女利益。
意思表示不真實(shí):
王粒作為未成年人,無民事行為能力,無法獨(dú)立作出贈(zèng)與意思表示。王先生代其簽訂贈(zèng)與合同,本質(zhì)上是單方意志強(qiáng)加,缺乏被監(jiān)護(hù)人真實(shí)意愿參與。
王先生未提供任何證據(jù)證明王粒(或其法定代理人)曾同意贈(zèng)與,其行為屬于虛假意思表示,符合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六條關(guān)于 “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(shí)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” 的規(guī)定。
違反公序良俗原則:
監(jiān)護(hù)制度的核心是保護(hù)未成年人權(quán)益,監(jiān)護(hù)人利用優(yōu)勢地位侵害被監(jiān)護(hù)人財(cái)產(chǎn),嚴(yán)重違背家庭倫理和社會(huì)公共道德。法院認(rèn)定該行為 “有悖公序良俗”,直接援引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三條,確認(rèn)贈(zèng)與合同無效。
類似案例中,監(jiān)護(hù)人以 “規(guī)避債務(wù)”“申請低保” 等理由處分被監(jiān)護(hù)人財(cái)產(chǎn),法院均以 “超出合理限度”“缺乏必要性” 為由否定其效力。
贈(zèng)與合同無效后,法律后果的處理需遵循以下規(guī)則:
財(cái)產(chǎn)返還與折價(jià)補(bǔ)償:
根據(jù)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七條,合同無效后,因該行為取得的財(cái)產(chǎn)應(yīng)返還;不能返還的,折價(jià)補(bǔ)償。本案中,房屋已出售給第三人且無法追回,王先生需按實(shí)際成交價(jià)款 1160 萬元賠償王粒。
賠償標(biāo)準(zhǔn)以 “填平原則” 為基礎(chǔ),旨在恢復(fù)被監(jiān)護(hù)人受損前的財(cái)產(chǎn)狀態(tài)。若王先生主張售房款用于王粒留學(xué),需承擔(dān)嚴(yán)格舉證責(zé)任,但本案中其未能提供充分證據(jù),故法院不予采信。
監(jiān)護(hù)人責(zé)任的特殊性:
第三人責(zé)任的排除:
訴訟時(shí)效未屆滿:
王粒于 2023 年發(fā)現(xiàn)權(quán)利被侵害,根據(jù)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八十八條,訴訟時(shí)效自權(quán)利人知道或應(yīng)當(dāng)知道權(quán)利受損之日起算,故其起訴未超過三年時(shí)效。
未成年人因法定代理人侵害權(quán)利的,訴訟時(shí)效自法定代理終止或新監(jiān)護(hù)人確定后起算。本案中,王粒仍未成年,其母親作為第三人參與訴訟,可視為權(quán)利救濟(jì)途徑的延續(xù),進(jìn)一步確保時(shí)效合規(guī)。
舉證責(zé)任分配:
王先生作為監(jiān)護(hù)人,需對 “處分行為符合被監(jiān)護(hù)人利益” 承擔(dān)舉證責(zé)任。其主張 “售房款用于留學(xué)”,但未提供轉(zhuǎn)賬記錄、留學(xué)合同等直接證據(jù),法院依法不予采信。
類似案例中,監(jiān)護(hù)人以 “資金混同”“口頭承諾” 等模糊理由抗辯,均因舉證不足敗訴,凸顯證據(jù)充分性在監(jiān)護(hù)權(quán)糾紛中的關(guān)鍵作用。
監(jiān)護(hù)人的‘絕對忠誠義務(wù)’:
未成年人財(cái)產(chǎn)保護(hù)的制度屏障:
法律對未成年人財(cái)產(chǎn)實(shí)行特殊保護(hù),即使父母作為監(jiān)護(hù)人,也不得通過 “贈(zèng)與”“代持” 等形式變相剝奪其所有權(quán)。
離婚時(shí)涉及子女財(cái)產(chǎn)的,需在協(xié)議中明確約定財(cái)產(chǎn)用途和監(jiān)管機(jī)制,必要時(shí)引入遺囑信托或監(jiān)護(hù)監(jiān)督人制度。
公序良俗原則的司法擴(kuò)張:
對監(jiān)護(hù)人的警示:
對被監(jiān)護(hù)人的救濟(jì)路徑:
對社會(huì)治理的啟示:
綜上,本案判決不僅是對個(gè)案的公正處理,更是對監(jiān)護(hù)制度核心價(jià)值的重申。它明確了監(jiān)護(hù)人的行為邊界,彰顯了法律對未成年人財(cái)產(chǎn)權(quán)益的剛性保護(hù),對類似案件的審理具有重要參考意義。
聲明:出于傳遞更多信息、利于普法之目的。本網(wǎng)部分內(nèi)容可能涉及轉(zhuǎn)載或摘錄于網(wǎng)絡(luò),但并不用于任何商業(yè)用途。若有來源標(biāo)注錯(cuò)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(quán)益,請作者持權(quán)屬證明與本網(wǎng)聯(lián)系,經(jīng)本網(wǎng)核實(shí)后將會(huì)第一時(shí)間做刪除處理。